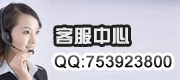没有方向感的“新盲流”们
“我们鞋厂数我学历最高。看仓库的本科大学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国头一个?”
站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平洲精旺鞋业有限公司的仓库门口,这个一头长发、颇有点艺术气质的大学生不忘给自己幽上一默。胡良奎是学广告专业的,当过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学生会副会长,自诩在大学里算是个才气纵横的另类人物,简历中,他声称著有长篇小说一部。
其实,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过几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给他1400元 / 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大学生至少也值2000元 / 月。此后他从合肥折腾到广州,又从广州、福州、深圳一路折腾到佛山。广州不少广告公司只给600元 / 月的底薪,深圳的一些广告和销售公司更狠,底薪一分不给,只拿业绩提成。他两手空空来到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进了这家鞋厂。现在,他的工资是每月800块钱。
近几年,中西部应届毕业生洪流,正在以越来越庞大的规模涌向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这一涌流与大学扩招直接相关。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2003年,第一批扩招本科生进入就业市场后毕业生成倍增长,逾212万。2005年和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各增长到330万与413万,分别是2001年的近3倍、近4倍。
然而,中西部的经济社会条件显然无法吸纳成倍上涨的毕业生。于是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工潮”之后,21世纪初,一股来自中西部的“大学生潮”开始形成,大规模地涌向吸纳能力相对较强的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国家人事部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仅北京、广州、上海、深圳4城就接收了人事部抽查的15个省市10.9%的高校毕业生。更有论者指出,近年北京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每年至少吸纳了全国高校一半的大学毕业生。
然而一个城市的吸纳力是不可能极速膨胀的。
随着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这股就业洪流由此变得曲折起来,一些就业支流甚至正在演变成胡良奎式的大学生找工“新盲流”。
“十元店”里的浮躁和勇气
历经几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宝安北路人才市场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费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学生正在陷入找工“新盲流”中。
他应聘的十几家广告公司和营销公司几乎都不给底薪只给提成,远没有他在合肥放弃的那份工作理想。他认为大学生就业价格的这种“贱卖”,与来深圳、广州找工的大学生太多有关。“人才市场和“十元店”附近到处都是背着包、拿着地图、脸色沉重的大学生”,他住在一个挤了14人的小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脚臭味。整栋“十元店”旧楼里,聚集了几百名来深圳找工的应届大学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时,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坐在对面一个劲儿地喝免费汤。胡良奎从旁人那里得知这是一位找工的大学生,现在没钱吃饭。胡良奎给她买了份快餐,结果女孩看着快餐就扒,痛哭失声。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应届专科生,父母已为她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她不满意,就辞工来深圳找梦想。结果工没找到,手机又被偷,身无分文。胡良奎劝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气,为什么就没有退回一步的勇气呢?”可她始终摇着头。
“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我发现不少大学生,包括我,来南方都是很盲目的。”于是胡良奎回到了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现在先在鞋厂做几个月,等五六月份回学校拿学位证时,我就辞工。这也是为了磨磨身上的浮躁气吧。”身处逆境的胡良奎还是想得很从容。
但广州南方人才市场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并没有胡良奎那样的从容与洒脱。
“十元店”里的应届生赵某,西安一所金融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是河南商丘的农村孩子。他说自己已在一家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资公司跑了一个多月,但还没拉到一单业务。“还想撑一个月,如果还没业务,那我真就弹尽粮绝了,只能先回学校再说。”他的大学4年是靠父亲刨地撑下来的,自己还申请了1万元的助学贷款。他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签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无脸见江东父老啊”。
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陆家嘴地段,也汇聚了100多名和广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学生。他们住在一幢破旧大楼第12层的简陋房间里,名称更时髦些,叫“求职村”。他们入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吃3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归,出门光鲜,归来垢面。几十人共用一台热水器,甚至栖身门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间的年轻人各怀心事。从内蒙古结伴而来的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蜷缩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两人甚至连简历还没做好,就冒失地来闯上海滩。这是他俩继天津后的第二站,给自己限期一个月。事后记者知道,当天他们按照报纸的招聘启事去徐汇区一家公司应聘,结果没找到,却晃到徐汇公园抽了半天烟。
同一房间里的徐州师范大学应届生任志杰,入沪4天来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底薪1000元外加提成。而去年毕业于燕山大学国际金融系大专班的宋国明,工作从天津找到上海,一个月薪千元以上的工作都没找到,几番在“十元店”里搬进搬出。
3月30日中午12时,钱财耗尽的宋国明将再次离开“驿站”。记者去送他,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有家公司愿给他一个月900块钱,包住,他没去,“在上海长时间找不着工作,人会疼的”。
陈示富,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整整在1204房间住了一个月,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在宋国明离开的那个晚上,陈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这城市与我有关吗?”记者捶了他两拳,说,再喊两声吧。这山东汉子竟真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然后扭过头,倏地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求职村”走去。
为何“宁要都市一张床,不要西部一套房”?
在这些外地找工大学生的意识中,京沪穗深这样的大都市,总是意味着机会、高薪和前途。以往他们的师兄师姐们以就业经验和日常信息,影响着他们产生一颗颗“都市心”。这无疑加剧了职业供给的不平衡,最需要大学生的地方少人问津,而都市的大学生求职者则人满为患
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岳昌君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2005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大中城市就业的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非大中城市。
因“都市心”形成的盲流,在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郑惠忠看来,是高校的就业指导和人力资源市场没有发挥好信息整合的作用。一开始就解决好这些学生与大城市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王明,因为专业不吃香,这位来自内蒙古农村的大学生觉得,以考公务员的方式留在北京是最好的方向。从去年开始,他数次参加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公务员考试,但最后总是被淘汰。前段时间,崇文区举办了一个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会。他去一看,有80%的岗位都只面向北京生源。没有户籍限制的民族宗教事务处,硕士生的简历也有一尺多高,本科生的简历更是好几摞。他最后连笔试机会都没得到。一星期前,他母亲打来电话:“人家都能找到工作,你怎么就不行?”当时他急了,手向走廊的玻璃上砸去。记者见到他时,他手上的伤还没好。
此后他不停地在网上和招聘会上投简历,一心想留在北京。现在的就业期望已降到有没有北京户口无所谓,只要能给2000元/月以上的工资就接受。他曾经想去山西,但他的母亲不同意。“村里人肯定会议论,谁谁家的孩子在北京念书,结果找工作反倒去了外地。”他说。
“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成了北京大学生们普遍的就业心态。中央民族大学就业中心一位负责人介绍,去年73%的毕业生都是留在北京工作,就业去向太集中于北京了,“像我们学校的学生,要是到其他地方,即使是省会城市都是很好找工作的,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去。”
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立平也介绍,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学校很多涉及林业技术的专业在基层林场用得上”,可去基层林场的毕业生几乎没有,“去了也养不住”。
而另一方面,北京市的《200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意见》规定,今年将继续执行京外生源本科毕业生择优留京就业政策,本科生留京比例仍限定在30%。 所以,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即使扩张到目前规模,也还没到大学生过剩分不出去的地步。像北京的大学生就业难,“更多地还是与毕业生千方百计要一个北京户口有关。”
这种情况也在上海出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某班的31个人,除考研的9人以外,剩下22人只有一人签约。一些外地大学生告诉记者,为了留在上海,他们甚至放弃户口,到缺乏保障的私立学校就业,拿1200元-1300元 / 月的工资。有学生移动着日渐宽松的表带,说:“最近都瘦了一大圈了。”
而在全国,北大教育学者岳昌君对2005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分布调查发现,该年七成以上的大学生在大中城市工作。但随着国家鼓励大学生去基层、边远地区的激励政策出台,这一年去县城以下的大学生比2003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
但岳昌君认为,大学生大量去农村还不太可能。由于目前制造业占很大比重,他认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吸纳大学生,这需要大学生转变“都市心态”的择业观念。
“面霸”、“考霸”传奇
在大学生就业压力之下,不但有暗潮涌动的“新盲流”,还涌现出富有传奇色彩的“面霸”、“考霸”,而往往是这样坚忍的同学,在7月来临前总能找到“婆家”。
3月底,广东海洋大学国贸专业的应届本科生吴锦方终于找到了一份1000元 / 月的营销工作,脱下了“面霸”的帽子。“面霸”是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一句行话,是指乐此不疲参加面试的人;“面霸”再被拒绝无数次而坚忍不拔的,就成了“拒无霸”。
为了在广州找到一份工作,吴锦方在今年2月份的20天内在网上投了近1000份简历,“连吃饭时都按着键盘投几下”。他得到过30多个面试机会,他赶了20多个,“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我就是部面试机器,从早到晚都排满了面试”。他对薪水的预期也随次递减,从1800元降到1500元,再降到1000元。“如果连每月1000元的工作都找不到,那我只有离开广州了。”他告诉记者。幸好,他最终找到了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的王胜德,被同学戏称为“考霸”。从去年12月25日起,他去过十几个城市考公务员,“国家公务员、检察院、法院、北京、上海、大连、福州、广州、深圳……”
为了考公务员,他已经花了5000多元,这3个多月中有2 / 3时间在路上、在东莞至广州的火车上,他站着复习公务员考试资料,再站回来。“在东莞,没地方住,我就和同学的哥哥一起挤在民工棚里,蚊子乱飞,屋子很暗。”“考霸”向记者历数奋斗史,还调侃了一下非“考霸”:“有个同学每次考总是离录取差一名。到最后考上了,却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3月31日晚11时,他最后对记者说,明天自己还要踏上去天津考公务员的路。
这位“考霸”其实是站立在一个庞大的数字前。据教育部门公布,2006年的公务员报考人数为127.5万。其中通过招考部门资格审核的公务员考生约为50万人,合格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约为43∶1,超过了2005年37∶1的平均报考比例。即400多万毕业生中,只有3%的人能实现这个愿望。
报告公务员因为这种激烈竞争而在各大高校里“白热化”起来。
武汉大学法学院300多名硕士毕业生差不多全部报考了公务员,最后被录取的只有五六个人,这几位“成功人士”成为年级里的传奇人物。
该学院的女研究生小罗告诉记者:“之所以这么热,是因为一个毕业生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像公务员那么稳定、体面、高薪的工作。现在工作实在太难找了,只要是个机会我们都想试。”
面对“面霸”和“考霸”的不易,一些毕业生自然要利用身份资源、亲友资源和权力资源。北京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李亮告诉记者,班上的北京本地同学找工作比他们容易,“10个北京人中就得有8个可以找到门路。”而武大法学院的一个男生,他姐姐在中石化工作,他就托姐姐的关系,最后也签到了那里。而中国政法大学一位学生告诉记者,他们在找工作中有着微妙的群体分化现象。农村学生、贫困学生没有家庭背景,只能不断积极地找工作机会。
与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岳昌君一同做相关研究的文东茅教授发现,“父亲的社会阶层越高,毕业生的平均起薪额也越高,父亲为农民者比父亲为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少400元和300元。”他们的研究表明,与2003年相比,毕业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网络在求职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尽管知识、学历和自身能力仍是就业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需要警惕这种不公平现象。”文东茅告诉记者。
名校生、博士生依然“好女不愁嫁”
清华大学2002级计算机系博士研究生蒋同学基本上不愁了:“清华学生找工作很轻松。 我们专业的毕业生主要去向依次是国企、外企和党政机关,进高校的很少,除非是留校,要么就出国做博士后。我们找工作很轻松,不存在问题。因为各个课题组与国内外大企业有很多合作关系,清华的牌子及导师的名气为我们铺平了就业大道。我们每个人一般只投两三份简历,现在每个人手上都至少有一个offer,如我就拿到了3个,我的选择标准是长远发展的前景。”
从复旦大学得到的一个数据是:2005年复旦全校本科生平均就业率为95.30%。其中通信工程、财政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新闻学等16个专业的就业率达到了100%。过去普遍认为男生在就业中占据优势,然而通过复旦在校学生职业发展在线所做的调查发现:2005届本科毕业生男女就业率存在一定差异,男生就业率为93.05%,女生就业率为97.96%,女生高于男生4.91个百分点。
复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许玫告诉《新闻晚报》的一位记者,男女毕业生对就业环境压力的应对,女性要高于男生。在复旦,从心理准备、在校期间能力培养、社会工作、实践活动的参与度等角度来看,女生表现出的积极性明显高于男生,这使女生在就业市场上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而博士生好像也不需要太愁。
华中科技大学2002级电机工程系博士研究生辛同学说:“我们班按时毕业的同学共有10个,全部进了高校,其中6个留在武汉、1个在长沙、2个在南昌、1个在广州。这些学校全部都是211以上,对于华中大的博士生来说,211是个底线。博士生找工作一般不会去双选会‘撒网’,而是一对一的联系,合则约见,比如,我就投了南昌大学和江西省电力局。我们找工作都比较顺利,虽然其间会被拒,但波折不算太大。这主要是博士生没有像本科、硕士那样扩招,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基本稳定;另一方面,高校持续扩招,相应的师资需求也有所增加,所以目前博士生就业市场基本上供需平衡。另外,高校的工资待遇不错,工作稳定,博士生一进高校便是副教授,且年薪都有三四万,待遇问题上东西部高校的差距并不大。据我所知,高校在选择人选上,重男轻女的情况并不严重,较之男生,女生当老师并无劣势。
|